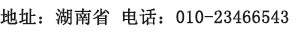已是深秋,天气渐渐寒凉。
白日里晴朗温和,穿得单薄一些,到的晚上,冷风便从裤管里往身上蔓延。
苏秋雨结结实实地抖了抖。
从河里将衣裳捞出来,用力拧了拧,感觉这水都冰冷刺骨起来。
她拧干衣裳,瞧着河里一个小小的马桶顺着河水往外跑,任谁也捞不出来了。
她站起身来,捶了捶蹲得酸麻的腿,准备往回走。
天已经黑了彻底,喧嚣的紫禁城里安静地落针可闻。
只远远瞧见远处的空中映照出一些颜色。
那里灯火辉煌,宫灯璀璨。
同为宫中,此处却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
眼瞅着宫道上一个人也没有,她攒着衣裳猫着腰,从宫墙根上往回溜。
“谁!”远处突然有人怒喝一声。
苏秋雨被惊地脚尖一抖,却头也未回,脚步加快,拼命往前走。
“说你呢!站住!”
尖锐的叫声被风吹到耳畔,那人越叫,她的脚步愈发匆促。
她穿着软底鞋,虽然步履匆忙,走到石板路上半点声息也无。
若不是寒风中走得快有些微喘息,只怕便是走在对面都不一定看得到她的存在。
直走了好一会,身后的喝叫的声音似乎消失了。
苏秋雨方停下来,浓黑的夜色里回头张望。
长风在宫巷里呜呜咽咽。
那人想必没有追上她,也便放弃了。
转头四顾,天上无星无月,四周一片黢黑,终于不远处有两只宫灯摇摇曳曳。
好险,方才慌不择路,差点便要撞上辛者库的宫门了。
若是惊动了人,今夜只怕不妙。
她拍了拍胸脯镇定了片刻,辨了辨方向,便往自己的宫室而去。
没行几步,突然斜刺里跑出个人来!
这人出现的突然,着实将苏秋雨吓了一跳,手里的衣裳都落了地。
那人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尖声叫道:“好呀!终于被我逮着了!”
说着从怀中掏出个火折子一点,一只半大的宫灯颤颤巍巍的点燃了。
照得他惨白的面色一片阴森可怖。
来人正是辛者库的净桶管事寻三。
火光下,他扯着嘴角讥笑道:“果然是你苏秋雨!方才我叫你,你是聋了?!为何我越发叫你,你跑得更快了!”
说着就将手中的灯笼往苏秋雨面上怼过来,恨不得直接抵靠到她的脸上。
苏秋雨习惯了黑暗,此刻光影照来,下意识侧头避了避。
“寻公公。”她微曲行礼,满脸惊讶地道,“寻公公怎会在此啊?奴婢正急着去交差,未曾听到您的叫唤。”
寻三细瘦的脸被灯影拉得好长道:“你还狡辩,苏秋雨!最近我就瞧着你行事鬼鬼祟祟,你一个洗衣裳的有事没事老去我净桶处徘徊,果然有鬼。”
苏秋雨瞪着圆圆的眼睛,无辜地道:“寻公公冤枉啊!我们浣衣所与您净桶处本就在一处,职事上也常有交互,奴婢并未特意去那处啊。”
寻三道:“你别巧言狡辩了!方才的事我都瞧见了。”
“方才的事?”
寻三晃着手里的灯笼,将那本就橘子般大小的光晕晃的人眼花缭乱。
太监特有的尖利嗓音在空空的巷道里左冲右突:“你当我没瞧见?你方才鬼鬼祟祟地拖了只净桶去了河边,将那净桶扔进河里去了!”
苏秋雨抿着唇未说话,一双浅淡的眼睛躲在阴影里看不真切。
“那净桶坏了,负责净桶的小元子今日无暇,知道我要去永河旁寻衣裳,便托我一并扔了。”
“是吗?”寻三的双目中透出令人作呕的神色来,“你倒是会狡辩。你当我不知你这些日子做了什么?”
苏秋雨在黑暗中抬起头,眼睛里一小簇灯火晃了晃。
寻三瞧见她的神色,心中没来由地一突,又见她瘦弱的身姿,不由呸了一口道:“这些日子你每日里浣完衣裳,就去帮小元子那小白脸刷马桶,怎么?你当我没瞧见?你是瞧上那阉脏货色了?”
“你胡说什么!”
“我胡说?”寻三讥笑道,“这些日子我就常见你一人行事鬼祟,老爱往净桶处跑,一定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今日天都黑了,你不在宿舍里好好呆着,又如此偷偷摸摸跑出来,还将桶扔了,你一定有鬼!”
苏秋雨道:“你还瞧见什么了?”
寻三道:“呵呵,还要瞧见什么?我估摸着你这件衣裳也有什么问题吧!”
地上墨绿色的衣裳皱成了一团。
苏秋雨方要说话,寻三得意地摆手道:“你且不要与我分辨,我这就带你去见石总管,让石总管好好审审你!大半夜的,你为何要扔净桶!呵呵,石总管审人的本事,想必你也知道。还不若此刻老实交代于我。”
眼见苏秋雨一声不吭,他伸手就要来拽人。
苏秋雨避让开他枯柴一般的手来,道:“你既然都瞧见了,那。。那我也无法了,只能与你到石总管面前走一趟。”
说着她弯下腰来,捡起落在地上的衣裳。
这衣裳虽然拧干了,但潮湿异常,此刻落了地,滚了满手的灰尘。
苏秋雨用力掸了掸,想要将那灰尘从衣裳上拍走。
寻三拧着灯笼催促道:“还不快点!莫想再逃!今日既逮。。”
话还未说话,戛然而止。
他感到脖颈处一凉,寒彻骨髓一般,心头惊跳,下意识伸手去摸。
什么都没摸到。
寻三方想是自己想多了,哪知突然心尖传来剧痛。
这痛如一个人徒手伸进了他的胸膛,用极长的针直接刺入他的心脏一般,尖锐而痛楚,痛到极至无法形容。
他从未想到此生连一呼一吸都是一种酷刑。
想要痛呼出声,双目暴突,嗓音却也如被人掐断一般,一点声息也发不出来。
所有的痛都被扎在了这副皮肉之中,半分外溢不得。
灯笼早滚落在了地上。
里头的火舌很快舔舐上薄薄的灯笼纸,卷出一片漂亮的灯花。
寻三轰然倒地,本就干瘦的身体未曾惊起一片尘土。
他倒在地上,突然抬头,瞧见苏秋雨比常人更白净的皮肤映着通红的火光。
他便倒在她的脚边,瞧见她漠然站着,静静地,居高临下地看着自己。
那浅淡的双目中,竟是妖艳的红。
这平日里温婉如江南烟雨的女子,此刻比阎王殿中爬出的恶鬼还要可怖。
“是她。”临死前,寻三脑海中咕咚冒出最后一丝念头。
咽下最后一口气,他心间一松,这痛楚总算是结束了。
苏秋雨看到他闭上了眼睛,那灯笼也烧成灰烬,被风一吹,四处飞扬。
她抱紧衣裳,摸了摸左臂,喃喃道:“瞧见了不应该瞧见的,还要说出来。。。”
巷道重又回归黑暗里。
深秋的寒意愈发的大。
怀里的湿衣裳晕染了她胸前的衣襟,她却仿若未觉,只是默默地往回走。
“谁!”
哪知不过一会,又有人呼和出声。
此次苏秋雨方听到声音心中一愣,立时停住了脚步,呆在原地一动不动。
黑暗里,一队铁甲侍卫,走上前来。因为腰侧皆挂着宝剑,与甲胄碰在一处,走起路来叮咚作响。
当首一人也举着灯笼照上前来喝问道:“是哪个宫里的?怎么这么晚还在外头?”
这些是紫禁城里巡夜的禁军。
苏秋雨当即弯腰做福道:“回大人,奴婢是辛者库浣衣坊的宫人,苏秋雨。”
说着也不躲避,微低着头,模样恭敬。
那禁军皱了眉头喝问道:“这么晚,怎么在此游走?”
苏秋雨将怀中的衣裳捧出,低着头恭敬答道:“奴婢是奉了浣衣坊石双姑姑的命。今日晚间收整衣物的时候,发现这件衣裳不见了,因是件极要紧的衣裳,想必是午后风大,被吹走了。”
“石双姑姑命我出来寻,果然在河里被奴婢给打捞出来了。”
那禁军一把拉过衣裳看了看,是件深蓝色的锦缎袍,想是哪位总管太监的衣裳。
他一把又将衣裳扔了回来道:“既是浣衣坊的,为何从那个方向过来?”
方才为了躲那寻三,苏秋雨埋头只顾走,确实已离了浣衣坊的方向了。
她心中思索如何应对,哪知那禁军已经抽出腰侧的剑来,一把用剑柄托起她的下颚,逼迫着她抬起头。
冰冷的剑身如冰块一般激的她浑身汗毛战栗。
“从实招来,莫要耍什么花招。”
苏秋雨被迫抬头,这才瞧见对方,那首领下颌满是胡须,一双眼睛却满是戾气,嘴角在茂密的胡须里噙着可怖的笑。
那眼神瞧着自己,分明就是猫戏老鼠的目光。
苏秋雨立时垂下双目,不再直视对方的眼睛。
只是两行清泪已顺着眼角滑落下来。
她抽泣着,面上尽是慌张无助,小声地哀求道:“大人大人饶命啊,奴婢。。奴婢不敢撒谎。”
说着脖子一动不敢动,忙自腰间摸出宫牌来呈上,声音发颤道:“大人请看,这。。这是奴婢的宫牌,奴婢也只在这辛者库活动,并未出到外宫去,大人若是不信,大可将奴婢送去浣衣坊石双姑姑处查问啊!求大人明查啊!”
她说着浑身微微抖动,显见被吓得不轻。
那禁军统领接过宫牌,眯眼打量了一眼。
这入夜宫人走动也并非什么异常,虽说各处皆会下钥,但是一宫之内,因着各位主子管事的需求,夜里也是允许在一宫内活动的。
只是也该苏秋雨今夜倒霉,这禁军首领方在上峰那里挨了训,此刻一肚子火气正没处发泄。
这宫人虽口口声声是奉了命,只是他好不容易抓住了错处,哪有就此放过的道理?
便是合宫规,那也去慎刑司分辩去!
当即将那宫牌收入自己袖中,命身后的人道:“这紫禁城关系陛下和太子殿下的安危,半点马虎不得。既是可疑人,且送去慎刑司好好查问!”
苏秋雨一惊,送去慎刑司!
那里是犯错的宫人所去之地,便是没错,去了也要脱层皮。
自己今夜行踪本就不可告人,若是被送到那里去,受刑也就罢了,可难保不会被查出什么来!
身后几个禁军不容她多想,当即就上来拿人。
苏秋雨暗暗咬了牙,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语气却从柔弱中多了些力道:“大人饶命啊!奴婢真的是冤枉的!奴婢只是奉命行事,一切都合宫规,奴婢职份虽微,但也是紫禁城的宫人,便是有了错处,也该浣衣坊及辛者库总管处置,再上还有内务府,哪有一声不吭往慎刑司送的道理?”
“您是禁军,这般拿我,若是被李总管石总管知道了,只怕因了奴婢一个小小宫人要生嫌隙。这宫中自有宫规,还望大人能网开一面。”
辛者库里虽都是贱奴,但是归内务府管辖,便是这辛者库石总管,在这宫中也是排得上号的人物,更别说内务府总管,那可是在贵人身边伺候的,自己今日搬出他来,只盼能让这人忌惮三分。
哪知那首领本就受了气,不敢吱声,如今一个小小宫人也敢搬出这些个东西来压他,不由更是恨得咬牙道:“连你这贱婢也敢教训我?”
说着更是怒意勃发,哪管这些,招手就要将人送走。
此刻原该忧惧,苏秋雨脑中却无端冒出秀才遇到兵这几个字来,一时反而有些想笑。
对方来人的双手如钳子一般紧紧箍住了她的双臂,就欲将她往慎刑司送。
苏秋雨看了看四周十几个人,知道多说再无用处,便停了挣扎,任由这些人拖拽着自己。
今夜要做的事已做成,不过是要多些波折罢了。
天上无月,露出繁星点点,四野漆黑。
只有这一行人手中的灯火在夜色里明明灭灭,与天上星辰交相辉映。
这天地之间除了风声,静极了。
“停手!”
突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一声,从万般寂静里传来,既轻且淡,只是那语气却又高傲,叫人违抗不得。
那禁军统领当即皱了眉呵斥道:“又是哪里来的混账东西!夜深乱闯,且敢管我禁军的事!”
他话音落,却见从拐角里走出一个人来。
那人信步而来,身型瘦削,披着一身黑色披风,手中提着一盏莲花样宫灯。
苏秋雨一眼瞧见那黑披风下,露出层层叠叠的白色袍脚,如流云堆雪,纤毫不染。
不知这袍脚的主人,是何等样人。
只是那人在灯火阴影里,什么也瞧不真切。
统领瞧见这人一身黑衣,兜头兜脸,当即怒斥道:“什么人,鬼鬼祟祟!还不速速报上名来?”
哪知那人提着灯,却停了脚步。
统领心中狐疑,提着灯笼往前凑了凑,一眼瞧见黑色披风下,镶金嵌玉的腰带,金色团圆祥云纹饰从黑披风中露出一点,熠熠生辉。
他心中一惊,目光微上移,面如暖玉,眉目如画,一双黑沉沉的眸色也正淡淡地看着自己。
轰然一声,这统领感到头皮发炸,浑身如过雷电所过一般,激灵灵抖了几抖。
他再不敢多看一眼,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太。。太太子殿下!”
他不过一个小小佐领,虽在禁宫中当差,但从未拜见过太子殿下,可他也知穿着这身衣裳规制,这样相貌的人,在这禁宫之中,再无他人。
其余禁军闻言具都一惊,也跟着扑通跪倒在地。
苏秋雨原就在地上,此刻听闻众人的声音,也呆在了当地。
那禁军统领想起自己方才的话,更是惊出一身冷汗来,一时声泪俱下,跪地咚咚磕头道:“臣。。臣不知是太子殿下玉驾驾临,臣死罪。”
赵玄亦提了提手中的宫灯,似乎要将光晕拿远一些,声音毫无情绪:“太吵了。”
那禁军统领忙磕头道:“是,是臣罪该万死!”
再不敢多言。
赵玄亦也不再多言,信步越过他,瞧见地上跪着十几个禁军,禁军当中跪着一个女子。
这女子穿着一身单薄的灰褐色衣衫,蜷缩在地不过小小一团。
瞧着瘦弱可怜,方才与禁军讲话的那股气势已荡然无存。
他步履不停,从众人中穿过。
声音淡淡地飘来:“既合宫规,还闹什么。”
“是。”那统领忙磕头应是。
赵玄亦往前行了几步,又停下步子回头道:“你既是要回浣衣坊,在前带路。”
说着望了望地上。
哪知那女子只顾埋头跪着,纹丝不动。
还是那禁军统领惊得浑身发抖,急地与那女子道:“太子殿下在与你讲话!快回话!”
苏秋雨从呆愣里回过神来,这才反应过来太子殿下竟是要去浣衣坊,还要自己带路。
她跪在地上磕了一个头道:“太子殿下恕罪,时辰不早了,奴婢还要赶紧去司库那里交差复命,与您并不顺路,请恕奴婢不能为您带路了。”
声音温小却字字清晰。
这一句话惊地周围的禁军们差点晕厥在地。
这是多大的荣耀,这宫女果然是出身低贱见不得世面,当真昏聩了!
那周围禁军生怕连累到自己,忙下意识往旁边挪了挪。
只留的那女子一个人孤零零跪在正中。
赵玄亦想也未曾想到居然会有人当众拒绝他,一时未曾反应过来。
他这才仔细去打量地上的女子。
只是这女子将额头埋在地上,只露出小小的脊背来,什么也瞧不见。
倒是一头乌发如云,随意扎着个单髻。
搁在额边的双手,纤细而脆弱,在灯火下瞧着格外白净。
不知这埋在地上的面容,是个什么模样。
赵玄亦反应过来,方要说话,却见一人银甲红缨,从黑暗里匆忙行来。
瞧见他,忙跨步跪地行礼道:“太子殿下,臣来迟了。”
是他的贴身护卫,王忠信寻来了。
赵玄亦点了点头,对地上的人道:“既如此,你且去吧。”
哪知苏秋雨闻言,却与一旁的禁军统领道:“大人可否归还奴婢的宫牌?”
那统领一听,忙自袖中将那宫牌抽出来扔给了她。
苏秋雨接了宫牌,当即又磕了一个头,便自地上爬起来,埋着头匆匆走了。
王忠信一惊,当即就要呵斥这不知规矩的宫人,哪知却被太子殿下一个眼神制止了。
赵玄亦瞧她背影匆忙又仓皇,不知为何想起落荒而逃四字。
这世上许多人想要往他面前凑,还是第一次有人瞧见他,逃得如此快。
倒是个聪明人。
还未想完,余光瞧见地上似乎有个东西?
王忠信也一眼瞧见了,当即上前,捡起地上的东西。
这来路不明的东西,他不敢往太子殿下面前敬献,只是自己先看了一眼。
是个藕荷色的荷包,瞧着就是个女子用物,想就是那宫人方才挣扎中脱落的。
里头手感有些重,传来沉闷的声响。
他一把打开了荷包。
从中居然倒出三粒石头。
王忠信将那石头在手中颠来倒去,又闻又捏,实在未瞧出什么特别来。
这瞧着就是三颗随手可捡到的最普通的石头。
那女子好端端的,装三颗石头在身上做什么?
王忠信眉心一锁,直觉其中定然有些异常。
遂双手呈到太子殿下面前,哪知殿下对此无甚兴趣,只是道:“带会你交给浣衣坊的人便是了,若是那宫人的,还给她就是。”
“是。”
行了多步,赵玄亦停下步。
王忠信忙低声道:“殿下放心,臣来处置。”
说完又道,“殿下,方才那个跑走的宫女,可要臣也一并处置了?”
哪知太子殿下并未应答,只往前去了。
。
石守成是个跛子,宫中人早忘了他的全名,背地里都叫他石跛子。
据说是早年在宫中伺候的时候,犯了大错,被生生打成了个残疾。
只是他在辛者库沉浮经营多年,到底叫他爬上了大总管的位置。
这日夜间,石坡子正在烤红薯,眼见要熟了正要剥了来吃,却有人急急地来敲门。
石跛子骂骂咧咧地走去开门,却见一向伺候自己的小太监白着脸道:“石总管,有贵人来了,指名要见你。”
石跛子一惊,忙佝偻着身子问道:“这深更半夜的,哪个贵人会到这辛者库来?”
小太监道:“奴婢也不知,瞧着神神秘秘的。”
石跛子一怒,啪地一巴掌扇了他的脑门:“你长着这双照子是做什么用的!看来得挖出来当球踢!”
小太监捂着脑袋委屈地道:“那里守卫森严,奴不敢靠近。听说已经见了好几个人了,来传话的倒像是。。像是。。。”
“像是什么!”
“像是龙虎卫的!”
这一惊非同小可,石跛子差点站立不住,好不容易扒住门框才没跌坐在地上。
“你说像龙虎卫?他们已经见了好几个人?见的都是我辛者库的人?”
“是。”
石跛子再不敢留,连手杖也来不及拿,只是道:“将那炉火看好了,可别把我红薯烤糊了,回来还吃呢。”
说着一瘸一拐地就慌张往小太监所指的地方去。
这龙虎卫乃是陛下及太子殿下的亲卫,二十四卫之首,独立于三司六衙,不光掌着主上的安全宿卫,更是直受命于主上,行一切事。
今日半夜三更来辛者库,不知是龙虎卫中何人。
只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日只怕是凶多吉少。
石跛子走路瘸拐,心中急跳,一边想着近日可有什么把柄被人拿捏了,一边脚下疾行,不过行了几步就摔了个大跟头。
还是小太监急急跑上前来,递来了拐杖。
行到那贵人所在,瞧见门口侍立着两人,果然穿着银甲,是龙虎卫。
而那大门紧闭,里头灯火摇曳。
石跛子四处皆是心跳,勉强扯出笑脸上前行礼道:“辛者库总管石守成奉命来见大人。”
哪知门口的守卫并不开门,只是道:“在此行礼就是。”
石跛子一愣,心中有些不快,自己怎么着也是正五品管事,便是龙虎卫的大人,也没有这般的道理。
只是他面上不显,却还是扔下拐杖,扑通跪地,对着那扇紧闭的门高声道:“奴婢辛者库总管石守全,拜见大人。”
赵玄亦坐在屋内,听得外头的通报,遂问道:“听闻你前些日子身上有些不好?”
石跛子回道:“谢大人关心,奴婢这半残之身,只管尽心伺候好主子们,哪敢有不好的时候。”
侍立一旁的王忠信眉心一拧,躬身行礼道:“太子殿下,这人不知是殿下亲至,难免胡搅蛮缠,让臣去问他。”
赵玄亦摆手道:“不必。”
王忠信不敢再说,只是退后一步站着。
赵玄亦指腹从茶盏沿上滑过,又道:“听闻你辛者库过去一个月,有几名宫人身染不适,你既无碍,为何没见上报?”
石跛子一惊,不想此次这些人是为这事而来。
他压下心头紧张道:“正是秋中转暮,天气乍暖还寒的,人就容易不舒服。这辛者库里都是身份低贱福气浅薄之人,难免就染上些风寒丢了性命。”
“风寒?”屋内的人声轻轻地飘出来。
听起来这人年纪不大,像个二十来岁的年纪。
石跛子心头稍定,这龙虎卫中几位有头脸的大人,年纪具都三十以上,想来这人也不过是个小佐领罢了。
想到此,他又道:“不敢欺瞒大人。这些个贱奴生了风寒,死也便死了,怎敢为此事去打扰各位大人们。只是大人今夜前来,便是问此事的吗?这辛者库人受寒而死,年年都有,不是什么稀奇事。莫说是辛者库,便是其他各司衙门,这紫禁城里上万的奴婢,哪日不死个人呢。”
还未说完,却听屋内哗地一声响。
赵玄亦一把摔了手中茶盏,平和的面色上一片寒凉。
一旁王忠信慌忙跪地道:“殿下息怒!”
赵玄亦心中怒火冲天而起,面色铁青道:“当真是恶奴,就地杖毙。”
“是。”
石跛子跪在外头,隐约听到里头的人声。
他竖起耳朵也未听见半句只言片语,过了半刻,听到有人行到门边道:“杖毙。”
什么?
他还未听清说的什么,哪知门口的守卫得令,当即架起他就往院中去。
石跛子心中预感不好,却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的命今日居然交代在了这里。
直到被架上了刑凳,他才脑海中啵地一声反应过来,知道经营多年,小命休矣,当即哭喊着求饶。
口中还不清不楚地叫着:“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你们不能杀我!。。饶命啊。。”
一时砰砰地行刑声惊地躲在周边的小太监们浑身发软。
不知过了多久,哭喊声方才消失。
赵玄亦寒着脸,负手走到屋外。
外头的守卫忙将地上的人拖走了。
王忠信又上前躬身道:“太子殿下,方才有人来报,在永安道里,发现了一个太监,已经死了好多时了。”
赵玄亦转头道:“永安道?”
“是。”
永安道是来浣衣坊的必经之路,按照时辰算,他方才途径之时,人已经死了。
“是如何死的?”
王忠信道:“臣方亲自去查看了一番,未曾发现伤口。又令人去寻了太医来,太医说他口歪鼻斜,想必生前极是痛苦,死时双手还紧紧抓住胸口前的衣裳,瞧这模样大体是死于心绞。”
心绞平日里瞧不出来,也无任何异常,可发作起来,是能立时毙命的。
赵玄亦道:“哦。”
转头却见王忠信欲言又止。
他原本心中怒极,此刻瞧见王忠信神情,愈发有些烦躁道:“你想说什么?”
王忠信忙跪地道:“经臣查问,这死的太监乃是净桶处的一个管事,名叫寻三。”
净桶处?
前些日子,这辛者库里染病所死宫人,大半皆出自净桶处,还有一些出自浣衣坊。
不过这两处原本就在一起,也分不出彼此来了。
今夜又有管事死于心绞,难道只是一个巧合?
王忠信禀告道:“今日那名宫女也是浣衣坊人,深夜出现在永安道,颇有些可疑。”
不知为何,他隐约觉得殿下对那宫人似乎有些青眼。
那个宫女?
赵玄亦无端想起她跪在地上的模样,在得知与那群禁军多说无用的时候,便安静了下来,停止了挣扎。
那弱小又认命的模样,却让他多看了两眼。
赵玄亦下了台阶行了几步,方皱眉道:“既可疑,还有什么好问的?一并拿了。”
“是!”
“此事干系,想必你也清楚?今夜也不必跟着伺候了,该杀的杀,该罚的罚,天明之时,孤要得到答复。”
王忠信一凛,跪地磕头道:“臣明白,臣必亲自查审众人,必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之人。”
。
苏秋雨裹着湿衣裳,一路疾行,直走到行坐宫外,方才住了足。
她喘了粗气,回头张望,深夜一片漆黑,早瞧不见任何人影。
黑夜里寂寂无声,仿若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心跳。
“咚”“咚”。
她深吸了数口气,好不容易压下剧烈的心跳,好一会才有些反应过来。
想起自己方才神色匆忙,落荒而逃的模样,当即自嘲地笑了起来。
果然,自己终究是个没用的人。
今日遇见了那个人,谁曾料想到自己竟会是这样的反应。
这些年来,在这座紫禁城中,她想尽了所有办法,也未能靠近那人身周半步,莫说靠近他,便是他住的文元殿,都从未有机会接近过。
这座城,太大了。
他们之间的距离,就如天壤。
谁曾想到今日却陡然撞上了。
她心中一时慌乱,便抱着头逃走了。
行坐宫内灯火还燃着,众人想必还未睡下。
她轻轻扣了扣门,果然有宫人应声,瞧见她来,那宫人只是斜着眼睛道:“去寻个衣裳怎么寻了这么久才来!石双姑姑已经等急了!”
说着一把扯过她怀里的衣裳,又皱眉道:“怎么是湿的!”
苏秋雨道:“青青姐姐,午后风大,这衣裳叫吹到河里去了。我们收衣裳的时候未曾注意,因此漏了。方才我出去去寻,好在这衣裳还在河里飘着,便给捞上来了。”
那宫人听见说着衣裳落了河,当即露出嫌弃来。
苏秋雨忙道:“姐姐无妨,奴婢已经洗干净了送来的。”
“算你识相,只是今日之事,是你自个儿要为我效劳,我可没逼你。”
苏秋雨笑道:“姐姐说的什么话,我在这浣衣坊里,全靠姐姐照顾着我,我才能活到今日。莫说只是帮姐姐寻个衣裳,便是替姐姐去死,我也心甘情愿呢。”
那宫人被她捧着,面上露出一丝得意道:“莫要花言巧语。”
苏秋雨闻言笑了笑,又自腰间扯了宫牌道:“这是姐姐的宫牌,特还给姐姐。”
宫人瞧了瞧宫牌上鲁青青三个字,正是自己的,遂收入腰间,抬头瞧见苏秋雨一双略显浅淡的眸子盯着那宫牌发呆,遂道:“你也莫要急,你在这浣衣坊里已呆了五年,想必不久石双姑姑便会允了你各宫行走的特权,也会赏你一块宫牌呢。”
苏秋雨笑道:“倒是多谢青青姐姐吉言。”
眼见鲁青青要走,她上前一步扯住了衣裳,瞧见鲁青青不悦地回头,忙又松了开来。
鲁青青不耐地道:“你还有什么话?”
苏秋雨欲言又止,淡眉聚拢。
鲁青青提起灯笼,照得对面的人原本就比常人白皙的皮肤愈发透明苍白,登时气道:“你可是闯了什么祸事?”
苏秋雨闻言肩头一耸,模样甚是害怕,好半天方低声道:“有一事实在不敢瞒着姐姐。方才我自永安道上来,遇上了几个巡夜的禁军。。”
“什么!难道你将我抖擞出去了?”
“那怎么能!这宫人冒领宫牌说什么都是死罪,便是打死我我也不敢认的。只是那禁军查问了一番,瞧见我是执着宫牌的,既合宫规,也未细看,就放我回来了。”
鲁青青听闻,瞪了一眼道:“既没认出来,怕什么!”
说完心中到底有些发虚,又想起什么转头来道:“这可是石总管的衣裳,他若是明日问起为何迟迟还未洗好,你可得自己担着。”
说着啪地一声关上了门,自拿着衣裳去向石双姑姑复命去了。
苏秋雨对着紧闭的宫门扯了扯嘴角。
不想今夜那人亲自来了,那石总管,那个石跛子,只怕他明日可不一定有命来向我问罪了。
她感到一丝寒风吹来,吹的胸口处一片冰凉。
这湿衣裳,早将她胸口染湿了大片。从外到内湿了彻底。
苏秋雨在寒风了站了好一会,冻得浑身发抖,寒气入骨,才紧抱着双臂回去了。
一路回了寝室,还未坐下,苏秋雨就感到浑身发酸,头晕脑胀。
同住的云娥跑上前抱怨道:“不是说就出去随便帮个忙,怎么去了这么久才回来!哎呀,手怎么这么冰。”
随手一摸,额头触手滚烫。
云娥一惊,忙将苏秋雨往铺上扶。
摸到她衣衫都湿了,更是恨的牙痒道:“你都这么大人了,怎么还穿着冷衣裳到处跑,这么不把自己的身当回事。”
苏秋雨却抓住她,小声地道:“方才在外头,我听闻有人在查问之前染了病的人。”
云娥圆圆的脸立时白了。
“我方才回来的时候留意了一番,凡是染了病没死的,或与染病之人有瓜葛的,都被带走了。”
云娥惊慌地道:“他们抓人去干什么。。难道还要处置掉吗?这些日子不是已经没有新的宫人被传染了吗?”
苏秋雨感到浑身疲累,半闭着眼睛道:“这个病传染性虽比不得天花,可到底还是会传染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沾了就去半条命。虽说这些人表面上都好了,可谁知还会不会继续传染?若是我,也会这样处置的,宫里毕竟人多,金贵的主子们也多,谁也不敢担这个险。”
云娥哆哆嗦嗦着道:“我。。我我我真的已经好了,不会再传染人了。”
“我知道,”苏秋雨安慰地拍了拍她的手,一双比常人浅淡的眸子盯盯地看着她,看得云娥头皮发麻方开口道,“但是此事你万不可叫人知道,否则明日被抓的人里便有你我。”
云娥带着哭腔道:“我生病那会全靠姐姐救我,瞒着所有人,否则我必也会被扔到那废宫里头自生自灭。谁曾想都已经过去了这么久还有这一遭啊。”
苏秋雨安慰道:“你也别急,只要你我守口如瓶,不会有人知道的。”
。
鲁青青方自石双姑姑那里回完,便高兴地往自个寝室去。
今日晚间突然发现少了衣裳,还是石总管的衣裳,石双姑姑急得不行,当即大发雷霆。
还是她自告奋勇,说一定要帮着给寻回来。
哪知傍晚时候突然降温,外头风实在冷得吓人,她不知为何又突然有些腹泻。
好在苏秋雨那小妮子主动前来示好,她也就将宫牌给她,让她偷偷代自己去了。
石双姑姑方才瞧见她将衣裳寻了回来,当着一众人的面,将她好一顿夸。
言语之中,颇有要提自己做管事的意思。
也不枉她这么些年,在石双跟前卖乖讨好。
想到此,鲁青青愈发得意,走起路来,都轻快许多,连腹泻都跟着好了许多。
方从行坐宫出来,突然黑暗里冒出个人来。
鲁青青不妨,吓了一跳,差点尖叫出声。
待看清来人穿着一身银甲,乃是龙虎卫,心中一惊,生生将惊叫给咽了回去。
那人上下瞧了她一眼,冷冷地道:“你叫鲁青青?”
鲁青青懵懵地点了点头道:“正是。”
那人又道:“今日晚间,你可出去了?”
鲁青青方要说没有,陡然想起那件衣裳来,忙改口道:“是,我出去了。”
“你出去做什么?”
“浣衣坊里有件紧要衣裳丢了,我出去寻衣裳去了。”说着想起龙虎军查问,忙又急急解释道,“那衣裳掉进了河里,我只是去捞了个衣裳就回来了,并未离开辛者库的宫门。大人,您瞧这是我的宫牌,可在辛者库自由出入,奴婢并未违反宫规。”
哪知她方讲完,却从黑暗里又出来一个人。
那人一双鹰目上下扫射自己,令她感到头皮发麻,心中狂跳不止。
鲁青青心中咕咚,冒出不详的预感来。
哪知那人点了点头道:“衣裳身形都不错,言语也对的上。拿下!”
鲁青青大惊,方要叫起冤来,哪知对方眼疾手快,已是将一团步塞进了口里。
她只能呜呜呜地再发不出半点声音。
鲁青青手脚被捆,口被塞了严实,被一人押着,扔进了一个黑漆漆的屋子。
这屋内一团漆黑,冰冷似铁。
她心下大骇,浑身战栗难言,如一块破布一般瘫软在地。
屋内满是她剧烈的喘息之声。
不知过了多久,那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丝光亮自门外照了进来。
一人手提油灯,长靴踩在冰冷的砖面上,屋内满是回响。
鲁青青双目圆瞪,惊骇地瞧着来人。
这人面目隐在油灯背后,面上一团漆黑,黑暗中感觉到一双黑眸如冰针一般刺往她的胸口,直如阎罗一般,登时令她魂飞魄散。
那人将油灯搁在桌上,便自坐了下来。
正是王忠信。
“你是何人?”王忠信问道。
鲁青青结结巴巴地道:“奴。。奴婢婢是是。。浣衣坊宫人,鲁。。鲁青青。”
王忠信手中正转着她的宫牌,问道:“你深夜出现在永安道,所为何事?”
鲁青青浑身抽搐,直想说自己并未去那里,可若查出她私授宫牌,那便是死罪,只得咬牙将去寻衣裳的说辞又说了一遍。
王忠信啪嗒一声扔了宫牌,问道:“还有呢?还不从实招来!”
“还。。。还还还有什么?”鲁青青大呼冤枉道,“奴婢实在没其他事了,真的只是去寻衣裳。”
“果然又是一个刁奴。”他手指微碾。
鲁青青这才瞧见这人身旁还悄无声息站着一人。
那人提着油灯走到一旁,墙上一排的长鞭尖刺等物,在黑暗里露出骇人的光。
“啊啊啊啊啊!”
。
“你听到了吗?”苏秋雨突然自高烧的浑浑噩噩中惊醒过来,轻声问道。
云娥本就担惊受怕未曾睡着,被她这突然的一声吓得一跳,结结巴巴地道:“听。。听听到什么?”
苏秋雨转了话题道:“若是有人对你用刑,比如鞭子,烙铁之类的,你能撑几个回合?”
云娥呸地一声道:“瞎说什么!我最怕鞭子烙铁之类的东西了!”说完又慌张地道,“难道。。难道有人要拷问我有没有得过疫症吗。。”
“我不过随口问问,你便随口答答吧。”
云娥哭道:“我的骨头最软了,莫说鞭子烙铁用在我身上,只怕刚亮相出来,我就全招了!”
苏秋雨瞧着窗户外头漆黑的长夜,喃喃道:“是啊,你的骨头软。不知她的骨头,有多硬呢?”
“若是受刑和挨打比起来,还是选择挨打吧,毕竟受刑那滋味,可是一辈子的噩梦呢。”
她声音小,云娥并未听清,此刻一心沉浸在自己要被人抓去拿问的恐惧里。
。
鲁青青虽是个粗使宫人,可到底是个女子,不过十数下,浑身便已皮开肉绽,不见一寸完好的皮肤。
她瘫软在地,连惊声尖叫都已不能了。
深秋天寒,额头的汗却如断线的珍珠,滚滚而下。
不小心落在伤口上,又是一阵酷刑。
王忠信瞧见她口咬的这么紧,一直喃喃说着同样的话,倒是有些意外。
“既只是去寻衣裳,我姑且相信你的话。只是你可知前些日子,你们辛者库有数名宫人染病去世之事?”
鲁青青一愣,原以为这些人只是在查她深夜行走之事,怎么突然扯到了染病身上。
便是这一犹豫,身上又挨了狠狠一记长鞭,钻心的痛。
她哭喊了一声,慌忙叫道:“奴婢知道!奴婢知道!”
“即知道,且细细道来。”
鲁青青边哭边道:“奴婢也只知道一个大概。便是一个月前,有个净桶处的宫人,突然半夜哀嚎不止,第二日就死了。那人毕竟年纪大了,死了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石总管便遣人将他裹了裹扔出去了。”
“可哪知不过第三日,那两个裹尸的人,也开始连夜哀嚎起来。”
“那时奴婢们都以为是招了那老头的邪祟,也没当回事,可哪知不过几日,接连又有几人染了病。我们才知此事非同小可,又怕这些人染的是天花,便上报了石总管,石总管查看一番说不是天花,我们才放了心,但是这病还会传染,石总管便命人将染病的人全扔到废宫去自生自灭。若是好了还回来,若是死了,便拖出去埋了。”
这些说辞,王忠信早在审讯的其他人口中听得,不过这些人众口一词,所言皆是如此,倒是没出现什么异常之处。
他冷了脸道:“这病除了辛者库,可传到外头去了?”
鲁青青慌张地道:“奴婢,奴婢是真的不知道啊!我们辛者库人是最低等的杂役,外人显少来,我们也显少出去,而且石总管虽然未曾上报,却偷偷地将染病的全都关了起来。。。”
说完又瑟缩了道:“不过。。不过。。”
“不过什么?”
鲁青青哭道:“奴婢记得奴婢小时候的家乡,若是有了瘟疫之类的,总是不知不觉便传的到处都是,不一定非要和染病的人呆在一处。。若是有其他宫的奴婢染上了,也不是不可能。。。”
王忠信听此言,一张脸愈发漆黑。
今日之行,关系的哪里是几个奴婢的染病去世。
那是改天换日的大事。
陛下不知为何,前些时日突然病倒,太医支支吾吾了半日,方说陛下可能是染上了疫症!
这一惊非同小可,宫中何来疫症?
何况伺候陛下的身边人,便是有个头疼咳嗽,也是绝不许靠近圣体的。
太子殿下秘密地亲查了宫中记录,才发现这辛者库一个月来,死亡人数颇多。
如今看来,这疫症,八成便是从此处传给了陛下。
只是辛者库人,便是石跛子,莫说没有资格面圣,便是靠近体元殿的资格也没有,又何能传给陛下?
“没了?”
“没了,真没了。”鲁青青瑟瑟发抖,差一点就要招出今夜偷换宫牌的事来。
可她入宫十多年了,知道若是此事抖擞出来,她在浣衣坊就完了。
王忠信自怀里掏出一个荷包来,伸到鲁青青的面前:“这可是你的东西?”
剩余61%未读立即解锁专栏,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