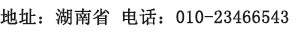谨以此文纪念我的虎娃叔,献给在中国农村这片土地上无数个普通而伟大的父辈。他们一生平凡普通,却为生活无怨无悔耗尽燃烧;他们看似木讷,却深藏担当;他们不善言辞,却柔情深爱。他们是她的父亲,他的父亲,我们的父亲。
——题记
1
多舛一生经磨难
虎娃叔是和我一起玩大的闺蜜亚亚的父亲,姓赵,彬州市太峪镇人,生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个身材矮小却永远有使不完劲的质朴农民。虎娃叔一辈子和妻子养育了七个儿女,三个早逝四个成人。为生存活命为儿女健康,几次举家搬迁,从彬州的断泾村到太峪马莲沟再到东湾村,构成了虎娃叔一生的生活轨迹。
虎娃叔最近殁了,年逾九十岁高龄的他,丢下了他含辛茹苦抚养成人的四个儿女和一群可爱的重子重孙,丢下了他把大半辈子的生命时光抛洒的马莲沟,寿终正寝,含笑九泉,也算是一桩喜丧。
回想起虎娃叔近一个世纪的人生,虽历经幼年丧父、早年丧子、晚年丧偶的种种不幸,但生活的风雨并没有击垮他。在他瘦小的身体里,因为爱,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并支撑着他在人生路上,一次次栽跟头跌倒,又一次次顽强勇敢地爬起。虽跌跌撞撞尝尽艰辛,却也是有情有义的完成了为人夫为人父的职责担当。一根细细的扁担,从断泾村到马莲沟,从马莲沟再到东湾村,挑出了一个令人起敬的老父亲形象。他为人一生,不善言谈,没有留下一句豪言壮语,他平和处世,不怨天尤人埋怨命运不公。他的一生,没干过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平淡无奇又伟大可敬,既没有轰轰烈烈的传奇色彩,更缺荣华富贵功绩过人的荣傲,但他就和我们身边无数人的父亲一样,用无怨无悔辛苦劳作,为妻儿撑起一片晴空,他不善言辞却心藏星月,他卑微弱小又强大深情。
2
马莲沟美玫瑰香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虎娃叔的老家在彬州断泾村。在他很小的时候,一场意外夺去了他父亲的生命,留下他和母亲相依为命,过着缺吃少穿恓惶的日子。在二十岁那年,因断泾村属于典型的川道地形,人多地少,山地贫瘠,没有家里顶梁柱头前人的母子俩在村上受尽邻人挤兑,恶妇欺辱,拉扯他的母亲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一咬牙做出了搬迁的决定。于是虎娃叔一根扁担便挑起了所有家当,带着母亲来到了太峪马莲沟。
马莲沟地处太峪,顾名思义,的确是一条沟壑深渠。但马莲沟地势偏僻加之山里居住的人少,可用来耕作的坡地多。虎娃叔第一次去马莲沟,转了大半天,当他看到沟底有一眼汩汩往外冒着水的清泉时,当即两眼发光满心欢喜的做出决定,要留下来!要在这个有土有水的地方扎根。几年后,勤劳的母子俩靠两双四只手开垦出数亩土地,又养了鸡兔牛羊等家禽牲畜。终于过上了自给自足有吃有喝的舒坦日子。
说起虎娃叔和会娃姨的婚事,还颇有几分浪漫色彩。那一年春天,正是梨杏开花,阳光明媚的好季节,干活高兴时爱唱几声秦腔的虎娃叔一边锄地一边扯开嗓子吼“手托孙女好悲伤,两个孩子都么娘,一个还要娘教养,一个年幼不离娘……”“哎——唱戏的,把你喔水给我们喝一口!能成吗?”猛听的有一个清脆的女人声音,朝着虎娃叔喊,像柿子树上的短尾巴花喜鹊,那声音脆生生的,在这个鲜有人来的山沟里,听着分外响亮,更透着一丝如蜜桃成熟时的甜味儿。虎娃叔猛不丁被这异样的人声吓了一跳,左顾右盼,才发现在他干活的斜坡上,站着两个女的。有个大一点的明显是姐姐,二十岁左右,手里提一个布口袋,两根麻花辫搭在胸前又黑又长,穿一件灰色的粗布衫,虽然好几处都打着补丁,但是满脸带笑有着长辫子的她,站在阳光里像极了一朵苹果花,朴素又美艳。她身边的女孩子小一些,看样子是妹妹,同样也穿着打满补丁的衣裳,一双眼睛怯生生的看着年轻的虎娃叔。
“你说啥?你要喝水?”虎娃叔朝她们喊。“嗯,我是坡头村人,跟我妹子去太朝村走亲戚了,她渴了想喝水,你喔瓦罐里还有么?”大一点的姐姐问虎娃叔。“唉,刚刚喝完了。么有了。”虎娃叔真的刚喝完了最后一口。“哦,乃就算了吧。”姐姐有些失望。转身拉起妹妹的手要走。“哎,要不我带你们去我家窑里喝,一大缸哩!”虎娃叔慌忙喊道。“你窑到阿达哩?远不远?”女娃脸上写满了疑虑。“不远不远,就在这坡上面,我妈今儿个在家蒸馍着呢。”虎娃叔说道。“蒸馍哩?你还有你妈?”女娃的眼睛里有了光,看了一下身边的妹妹,妹妹的嘴唇干干的,用祈求的眼神看着姐姐。说实话,当听到“蒸馍”两个字时,姐妹俩的嘴里都不争气的流出了口水,肚子也开始咕咕叫,越发感觉口渴了。“好吧!咱去你窑里喝口水。走——”“看你说滴,我咋能没有妈!我妈人可好呢!你不信等会见了人就知道了!是个人咋还能么妈!”虎娃叔对姐姐的问话故意表现的不满起来,嘴里嘟嘟囔囔。“噗嗤”一声,那姐姐不好意思地笑了“我就说这烂沟里咋还有个人唱戏哩,原来唱戏的还有个他妈哩!”姐姐居然很幽默,笑着打趣。“你甭看不起我这山沟沟,一年四季啥都不缺,看不完的风景。还有一眼甜津津的泉水,好着哩!”虎娃叔略显得意地夸起他的马莲沟。“能有多美?我想冬天肯定连个人影影怕是都见不到!”姐姐笑着怼虎娃叔。“咦,见不到人,可能打哈野鸡野兔么!放上一把盐丢锅里煮熟了,那味道香得很!你们肯定都么吃过!”肩膀上扛着锄头的虎娃叔一脸兴奋。转过头偷偷瞅了姐妹一眼,那姐姐的脸笑的红扑扑的,妹妹的嘴巴更干了。“听你这么一说,你这烂山沟沟里,还好得不行!”姐姐说。
“我说的是真是假,你住几天就知道了!哼,还不信!你喔烂坡头我去过的,就不是有十几户人么!都没有一片平坦的地,那一年的收成能够吃?”虎娃叔问。
“唉!就是吃哩不得够了,我妈让我和妹妹去太朝亲戚家借面了。”姐姐说这话时一下子就难过起来,整个人立时显出了和她年龄极不相符的生活的沉重和忧虑。
说话间,不远处的槐树上悉悉索索地晃动着一只身影,虎娃叔手放在嘴边,用眼色示意姐妹俩不要出声,只见他从腰间取下一个铁丝弯的弹弓,又从口袋摸出一个钢珠子,他闭着一只眼睛,屏住呼吸瞄准了那只身影,只听见“嗖”的一声,钢珠子穿风而过,不远处的树上就啪地掉下来一只圆滚滚的野鸡。这一番帅气的操作,可真是看傻了站在一旁的姐妹俩。姐姐朝着虎娃叔竖起了大拇指,嘴里却说“你心可真狠毒!那可是一条命啊!”
“切!只要能填饱肚子享受美味!我这马莲沟里,有我打不完的命哩!我就不信你不爱吃鸡肉?”虎娃叔白了姐姐一眼,憋着嘴笑。
一旁的妹妹兴奋地跑过去,捡起地上的野鸡,高兴地喊“姐,姐,快看,这人本事大哩很!”
到了虎娃叔半山腰的家里,三孔窑洞一字排开晒着太阳,整洁的小院里几只鸡扑棱着翅膀,院门口的树上拴着一头黄牛,后腿前偎依着的一只小牛正撅起屁股拱着在吃奶,羊圈里的羊咩咩叫着。小院门口有两棵不高的桃树,此时桃花正艳,姐姐忍不住摘了一朵放在鼻子上闻,虎娃叔却叫了一句“这是我栽的桃树,秋天等着要吃桃呢!你摘了我的花就要少结一个桃!你赔我!”“哼!我不赔!我拿什么赔?”“拿你么!”虎娃叔坏坏地笑着。“去去去!你这个人讨厌得很!”姐姐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一只黄狗看到生人戒备地“汪汪”狂吠着从院子里飞奔着窜过来,吓得姐妹俩抱作一团。“去去去!虎子你这蠢货,看不着是我引着哩吗?”虎娃叔拾起路边一块土疙瘩,一边骂一边朝着那只被他叫“虎子”的黄狗扔了过去,不料想那虎子却并不躲远,反倒亲热的偎依到虎娃叔的脚跟下蹭来蹭去,再不理会身旁的两姐妹。
虎娃叔的母亲是个贤惠善良的妇人。闻听两姊妹是太峪坡头人。姐姐叫宋会娃妹妹叫宋会娥,家里正青黄不接,今天是去亲戚家借面空手而归,更是一番热情招待。又是取核桃柿饼,又是端水拿枣,还端出了自己刚刚蒸好的大馒头外加一碟油汪汪的红辣子给饥肠辘辘的两姐妹吃,一时感动地两个小姑娘抹着眼泪,一口一个姨一口一个姨的说着客气感谢的话。最后虎娃叔母亲把自己蒸的馒头全部塞进了姐妹俩的布口袋,还从面缸里舀了多半口袋新磨的面粉送给她们,又安排儿子虎娃给背到了沟口。两姐妹一番感谢后道别。
在那个缺吃少喝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马莲沟俨然是人们心目中的一处世外桃源。有多少人都曾经有着对马莲沟的向往。可是,谁都无法舍弃太峪街道的繁华便利,谁都没有勇气从山外住到山里去。因而,马莲沟一直保持着她的清静与富足,一年四季,春有百花秋有果,有多少辛劳付出,土地就会有多少加倍回馈。
好人自有好报。不久后一向沉寂马莲沟就迎来了两位贵客。一位是宋会娃的母亲,一位是她的父亲。他们是专程来感谢这对心地善良的母子俩的。就在三个人坐在院子里说话时,满头大汗的虎娃叔挑着一担水回家了。会娃姨的父亲弯腰凑近水桶,用他粗粝的掌心掬起一捧水喝完,啧啧称赞“水是好水,娃是好娃啊!”后来,两家大人话说着说着,虎娃叔便有了媳妇,会娃姨便有了归宿,没有媒人,但两个年轻人其实自从第一次相遇,便早已是情投意合。谈婚论嫁自是水到渠成之事。
会娃姨嫁到马莲沟进了虎娃叔的窑门,这个山沟沟的小院子立时充满了生机。小夫妻男耕女织,男挑水女浇灌,肩并肩一起劳作,头抵头一起吃饭。看着恩爱的小两口,虎娃叔的母亲更是乐得合不拢嘴,把会娃姨爱的像自己的女子一样。虎娃叔人虽然个头不大,却浑身有一股使不完的力气,他眉眼带笑满脸欢喜,一天到晚的唱着那几句老戏词,腿下生风般越发勤快能干。
3
连丧三子黄连苦
第二年的秋天,眼看着身怀六甲的会娃姨就要为赵家添丁进口,虎娃叔的母亲却突然得了一种怪病。她身上的骨头奇痛无比,尤其是腿膝盖和胳膊肘,发起病来一阵一阵钻心的疼。虎娃叔两口子慌忙用架子车拉着四处求医问药,还送到了几十里外的老彬县城去看当时有名的医生。但是所到之处大家都摇头表示没有见过这种病,个个摇头做无奈状。没有办法,虎娃叔只好拉着老母亲回了马莲沟。最终,老母亲还是没有熬过那个冬天,没有等到见孙子一面,抱憾而逝。
会娃姨生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两口子疼爱有加视作掌上明珠,取名桃花。小桃花长得眉清目秀,一张白白净净的瓜子脸上,五官生的找不出半点瑕疵,但凡见过桃花的人都啧啧惊叹她是个美人胚子。虎娃叔自是宝贝疼爱,无论走哪,不是牵着桃花的手,就是把她架在自己的肩头。小桃花也可爱,咿咿呀呀地学着说话,虎娃叔就教她说“我家在马莲沟,我是马莲沟人。”后来,会娃姨又生了一个儿子,小两口的日子更是和谐美满,悠哉自在。
天有不测风云,桃花长到十五岁的时候,虽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但时不时的会喊着腿疼肩膀疼。这让虎娃叔两口子心头如同压上了块石头,回想起折磨老母亲当年的怪病,两口子心里就会罩上一团阴影,总是唉声叹气转辗反侧,夜不成寐。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就在桃花刚过了十六岁生日没几天,在给猪割草时,因为全身关节奇痛难忍,她一头栽倒在地,割草的镰刀正好扎在了手腕动脉处,鲜血汩汩的冒出来。等到虎娃叔赶到时,可怜的桃花早已经昏死过去没有了气息。可怜的虎娃叔抱着他的女儿桃花,用手捂着伤口,大声吼着“娃呀!娃呀!你这是咋了嘛?”哭的死去活来。这一意外变故让虎娃叔如雷轰顶,伤痛欲绝。他抱着比他还高出一头的女儿尸体,哀嚎痛哭了一天一夜,直到嗓子哑了泪流干了,赶来的亲戚才硬是扳开他紧紧抱着女儿的手,把桃花用草席卷了抬出去草草埋掉。那一年,虎娃叔才三十多岁,痛失爱女的他却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经常一个人坐在桃花的坟头,默默地叼着烟锅抹着眼泪,一句话也不说。
搬离马莲沟的决定是在虎娃叔和会娃姨生的第三个孩子夭折后做出的。那一天,又是一年花开时,桃李芬芳,棠梨生香。一大片绿油油的麦苗在阳光下拔节疯长。一群花喜鹊拖着长长的尾巴在山林间飞窜穿梭。马莲沟里正是一年春好处,而虎娃叔两口子却是肝肠寸断,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院子里猪羊在圈里饿得乱拱,鸡兔也没有人照料。窑门大开着。在马莲沟向阳的一片坡地上,小两口悲悲戚戚哆嗦着双手亲手埋掉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加上虎娃叔的母亲,这里已经立起了四个坟头。桃花之后有一个弟弟,因为一次生病拉稀不止,严重脱水后夭折。最后这个是一个已经长到八岁的男孩,虎头虎脑的他已经跑跑跳跳,可以帮母亲喂鸡喂兔了,可悲剧又一次降临这个早已伤痕累累的小家庭,他在一次发高烧后上吐下泻,不久后还是随着他奶奶和两个哥姐撒手而去。留下了枯瘦如柴两眼空洞无神的虎娃叔。会娃姨更如同一棵被苦难抽干了水分的树,头发枯黄,脸色蜡黄,她越发消瘦,似乎一不留神就会被一阵大风卷走。
虎娃叔看着失魂落魄的妻子,看着她怀里睡熟的小女儿,把手里的烟锅在鞋底哐哐两声狠敲,从口里吐出来几个字“咱搬家!咱要走出这马莲沟!”
“啊!你说啥?这么好的地方有地有水养活着咱,吃喝不愁住的好好的,搬阿达去呀?”会娃姨抹着眼泪问。
“我三个娃娃都埋在这里了!这地方好个?!咱要让娃活命,就要搬家!走走走!咱离开这马莲沟!咱到太峪街上去住!我就不信,别人能活咱就活不成!”一向不发脾气的虎娃叔生平第一次爆了粗口。
“可太峪咱么地呀,去了种啥?吃啥?我不去,我就要住在这马莲沟!”会娃姨被早些年的穷光景饿怕了,一个劲的摇着头。
“我今儿个给你把话说清楚,早都有人给我说这马莲沟底的泉水有问题,吃了对身体不好!是我一直舍不得走,才让咱妈和娃送了命!我有罪啊!我不该啊!会娃,这次你就乖乖地听我,咱搬家吧!你以为我就舍得离开,舍得撇下这个家吗?你要知道,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早已经都像是我的亲人!这里的每一处土地都浸着我的汗水,都是我一片一片开垦出来的!这里还埋着我四个亲人呀!四个呀!”虎娃叔跪在地上,双手抱着会娃姨的腿,一边摇晃着一边磕头,他疯了般的自责着,恳求着。
会娃姨呆住了,惊恐地望着眼前这个痛哭流涕捶胸顿足的男人,他曾经是那么坚强,那么乐观的一个庄稼汉。如今,却像一个无助的孩子。会娃姨心软了,机械地点了点头“好,我听你的,咱搬家!为了咱娃!”
搬走的那天,虎娃叔和会娃姨抱着四女儿,在马莲沟山坡上的四个坟头前,长跪难起。会娃姨哭着说“妈,桃花,我也不想丢下你们,我不想走啊!”虎娃叔手里捏着一根树枝,拨拉着燃烧的纸钱,满脸泪水,低头不语。忽然,一阵风吹过,卷起还未烧尽的纸灰,向马莲沟口的方向飞去。虎娃叔猛地仿佛醒悟过来,他用袖口擦干眼泪,咚咚咚地连磕三个响头。“妈,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带会娃和娃走呀!您放心吧!您等着我!”
作者简介:杨小云,彬州市人,喜欢写字,摄影。彬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全民阅读彬州悦读会会员。
扫描